作者:怅怅
连续两天跨城观看了两部作品:伊朗剧作家、导演南星·苏雷曼波尔的话剧《南星》和孟加拉裔编舞家阿库·汉姆作为舞者的封箱之作《陌生人》。一个北京一个上海,一个戏剧一个舞蹈,却因为创作者的少数族裔身份和跨文化的创作而遥相呼应。一个生长在政治环境特殊的伊朗,最终走向世界用外语写作剧本,一个出生在英国却因孟加拉裔背景与印度舞血脉相连,他们都成功地在“非母体”的文化中闯出一番天地,而各自的母体文化是他们甩不掉的羁绊,也是他们生长的养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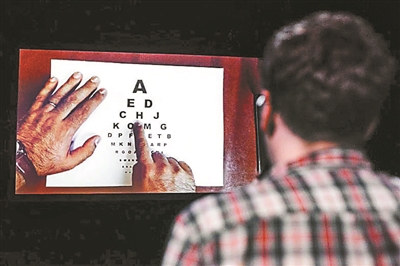
《南星》剧照 摄影/David Montreith-Hodge

《陌生人》剧照 摄影/Jean Louis Fernandez
“耶可以布的,耶可以纳布的”
《南星》在北京中间剧场上演,编剧的剧作《白兔子,红兔子》曾在北京演出过,这次的作品则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并且他本人也来到现场演出。与《白兔子,红兔子》的演出形式一样,还是不让演员提前看到剧本,也没有事前排练,全凭临场发挥,而且一部剧一个演员一生只能演一次,从演员到观众都因为这样特殊的形式而进行了一次从不明所以到融入其中的过程。这样的独特形式也源自现实的无奈,编剧因为拒服兵役护照遭到伊朗政府扣留而无法出境,于是用邮件将规则严密的剧本发往世界各地,由当地剧院制作和演出,以这种特殊的方法控制舞台,实现作品的世界“巡演”。
《南星》是编剧已经可以离开伊朗故土,定居德国之后的作品,因为有了之前的“兔子”,这种形式已不新鲜,真正打动我的是导演的创作初衷:因为一直用外语创作,虽然在世界上越来越知名,但是他的妈妈连他的一部戏也看不懂。于是他为妈妈创作了这部作品,在剧中让各国演员用特殊的方式把他的故事念给妈妈听,也让世界各地的人通过各式荒腔走板的发音,体验他的妈妈因为语言障碍而无法理解儿子作品的感受。
作为剧作家本人,南星在台上一个字也没有说,却用那厚厚的500多页纸和投影仪里多毛的一双手,把一切都说了。这个故事是献给“妈慢”(波斯语里“妈妈”的发音)的,但同时母亲在这里也成了一种象征,一种对于母体文化从疏离到回溯到融为一体的过程。“耶可以布的,耶可以纳布的”(很久很久以前),当中国演员用这样好笑的发音讲起这个故事,好像我们和导演一起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也好像我们无须跨越,而是在这障碍之上开出了新的花朵。
“哒个哩个哒,哒个哩个哒”
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的舞蹈大师阿库·汉姆的封箱之作《陌生人》,宣传中提到将有好几百个松果从天而降,这样的舞台实在太有吸引力,但是当看完全剧,征服我的却是极致的身体和深刻的思想,这不仅是作品,更是阿库·汉姆他自己。
这部舞蹈取材自一战中殖民地士兵的历史资料:在这场战争中有超过四百万非白人士兵被欧洲和美国雇佣,并客死异乡,而活着回去的人也与自己的历史、故乡和同胞产生了隔离,成为“陌生人”。舞蹈讲述了一位殖民地士兵在遭到炮击后进入迷离梦幻的精神世界的景象。
作为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纪念艺术委员会委约、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联合委约制作的作品,《陌生人》可以说是一个命题作文,然而抛开战争的部分,它更像是阿库·汉姆为自己、为自己的艺术生涯作传。那些飞快的旋转、自如的身体、低沉的重心、先锋的勇气,来自东方印度舞的传统,也来自西方现代舞的精神,他的身体、他的创作力都如同两者淬炼而出的独特艺术品,敦厚深沉地扎根在属于自己的那一片沃土里。
演出正式开始前,两位乐手在舞台上进行暖场表演,“哒个哩个哒,哒个哩个哒……”乐手用20分钟建立起的印度舞氛围在开演的一刹那便被炮火声击碎。阿库·汉姆扮演的士兵牵着一根绳子突然摔倒在台口,被一阵炮击摔进了臆想的世界,身后是一个巨大的斜坡,前面陈设着印度式的日常家居,在炮火和枪击声中两位乐手的鼓点执著地继续着,士兵从那陌生的异国战场来到这充满故乡声音的地方,不自觉地跟着鼓点跳起卡塔克舞步,脚腕上密密麻麻的铃铛叮当作响。然后他解下铃铛,一头系在脚腕一头拴在脖颈成了枷锁,他成了戴着镣铐起舞的人。最终,当他能够彻底解下铃铛之时,却把它们高举过头如宗教仪式般虔诚地置于脖子上。那些来自根系里的、束缚你、被你拼命摆脱的东西,最终都会变成信仰,变成你珍惜的一部分。
随后,舞台上的桌椅板凳各色陈设都被斜坡后伸出的绳子拽走了,任主人公如何追赶阻止也无济于事。泥土从斜坡上缓缓落下,除了这土,好像再不能拥有家乡的任何了。之后的整个舞蹈中,阿库·汉姆一次又一次不停地在这些泥土中翻滚跳跃,土沾得他全身都是,在他白色衣服上,在他卷曲的黑色胡须上,在他汗湿的光头上……
舞台上出现的那些绳子,在我看来都如同脐带一般是与自己母体文化的连接,而斜坡则是战争中的壕沟,也是难以逾越的文化障碍。当大绳子与象征外界声音的收音机连接到一起时,喇叭里传出人声,时而如军情播报,时而如部队点兵。主人公听到印度鼓点就不自觉地起舞,听到部队口号又迅速立正,在两种状态中来回切换,一如我们秉持着传统文化进入到其他文化中去的时候,那种不知道该把头摆向哪一边的不知所措。
最终,那些大大小小的绳子被主人公拧成了一股系在腰间,借着绳子坚实的拉力,他可以走下斜坡捧起一抔故土,也可以登上顶峰把绳子一圈圈围在头上起舞。
现场音乐也呼应了这一主题。乐队总共出现了三次,配置都是大提琴、小提琴、萨克斯和印度鼓及人声,每一次他们都出现在斜坡的顶端,从最初的嘈杂混乱各自发声,到中间的一度和谐再陷入混乱,最后来自不同世界的声音终于能够共鸣到一起,如同一次面对不同文化时对自我的调校过程。
临近结尾时,几百个松果从斜坡上缓缓滚落洒满了舞台,也终于到此时,我们才看到阿库·汉姆从身体到精神在紧绷了一小时后终于放松下来,历尽千辛万苦才将自身各种元素协调到和平共处的状态。采访中他说这些松果象征死在异乡无法被埋葬的雇佣兵,他们在异国他乡作战,最后死在异国的土地上,裸露在外的松果就像士兵们的躯体。而在我看来,它们也如同所有身在异国、于不同文明中生活劳作甚至付出生命的人们所结出的果实。这些果实也将变成新的种子,在新的土地上生长出参天大树。
每条小船都在碰撞中前行
阿库·汉姆说:“过去很多年里,西方人都把自己视为中心,认为历史是由他们来写的,事实上,其他文化也可以诠释历史,中国人可以,印度人可以,非洲人也可以。”某种程度而言,现代艺术对人友好的一面正是体现在这种跨文化的普适中吧。试想如果看不懂印度舞那些复杂的手势,不知道印度教中那些神祇和传说,那么看到古典印度舞的时候,获取的感受必然是骤减的;如果听不懂伊朗语,当我面对一个伊朗导演的传统戏剧的时候,也许会同样流失掉很多信息。但是当面对的是一个现代表现形式的艺术作品,这些缺失却可能也成为我观演的一部分,它带给我的比深谙这种文化的人感受的不一定会更少,反而还可能会因为这种缺失而更加丰富。
在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读到蒋勋的一段话,仿佛也正是这两部戏的一个注解:“一艘船必须先知道它是纯粹独立的个体,它并不属于码头,也不属于港湾,它也同样不属于海洋;但是,当它认识到了自主与独立,它才可能选择码头,选择港湾,或选择海洋。”
其实跨文化是一个可大可小的概念,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之间的是跨文化,不同地域不同城市间的也是跨文化,甚至在职场面对的与从小家庭教给你的价值观不一样,也可以是一种跨文化……不用上升到世界两个角落的高度,我们每一日的日常生活便都是在各种不同文化、不同观念、不同习惯之间或大或小的碰撞中前行着。某种程度而言,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有着不同的经历,在不同经历中汲取到的不同内容,拼凑出了独特的每一个人。而当艺术以一种更加凝练而极致的形式,将不同文化以更加可感的通道,输送到这个越变越小的地球上的更多地方的时候,无论是“耶可以布的,耶可以纳布的”还是“哒个哩个哒,哒个哩个哒”,都散发出了比以往更美丽的光华。(怅怅)
